每每一见着豆腐,或是腐乳,即能想着的就是父亲的一幕。
在少小时,那段难言的岁月,如今却早已变作了人们轻松唠嗑的话题。生活的艰涩,是诺大的整个一块土地上有且共有,并且统统无声承受的特绝景象。即便缺衣少食,依然是豪气干云地与天斗,其乐无穷。
那会儿依山面水的小山村中,虽不能优越出别的地方许多,但,从也未被饿着过,至少我少小的记忆里是。而更是特别的记忆——娘连杂面也很少让我吃的。虽是弟兄姊妹几个,老幺的我——就连长我几岁小姐姐也是从不与我争的 ,以致于后来的独生贵族们,在我面前只剩有冷齿的份儿了,——往后腾。
在那般的光景里,依然清晰地记着,冬日的时光里 ,在早饭的时刻,总有卖豆腐的挑着担子,吆喝着“打~豆腐~”,过村穿巷,来到院中。父亲偶尔会要上三二分钱的或是用一个鸡蛋换得块豆腐来,放在娘刚刚才从做馍(贴的死面饼为多)的锅里端出来的炖熟了的热腾腾的酱豆碗里,再用筷子摁压几下,便就着吃了起来。那时的我并未觉着它有多好的味道儿。就是这样,也免不了要听上娘的几句叨叨“偏要换个什么豆腐!”
今天的我,也稍稍才觉出了些些豆腐味儿的朴实来了。恁地想起,便是酸涩而不能语。父亲的一辈子中,在我费了许多的气力也搜寻不得出哪一样是父亲一生所喜爱的食物来,——粗茶淡饭,麻布葛衣,淡默无厉,虽也还能准确背出八年私塾刻记在脑海里吹散不去的“一箪食,一瓢饮”给我听,劳作不息,直至耄耋归山。
要用多少的语言可以记述得了父亲呢。然而,山风百转,所有的过往都将翻化无踪,直至明天的我,尚恐远不及父亲的一多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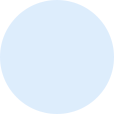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